听雨,在三坊七巷
苏小玲
一
这趟返闽滞留甚久,并遭遇了福州空前盛夏,一番“火炉”体验,堪比爬过的新疆“火焰山”!原本,在干燥缺雨的北方,总巴望能听一场无止尽的雨,淅淅沥沥,似音乐倾诉,如情人缠绵。那不是什么浪漫,是很现实的对排遣、解压的期待。不料转到眼下,再撞难忍的炽热,愿望更是强烈;等雨,等一次疗伤与慰藉。
连续数日,每晚我都会问一声妻:明天会有雨吗?
俩朋友,写小说和写旧体诗的,说是在这家三坊七巷的“书局”碰面,我先来了一步。记忆中的林则徐故居格局宏大,有若干进,视线都很开阔,哪个屋子的场地都很宽敞。单人置身,会觉得是围棋盘上落下的第一颗棋子,但若想让身体舒展自由,便能随心所欲。而眼前这座,虽规模不大,但前后左右也是处处透着敞亮。书局的主人巧为利用,厅堂主体,设计成既能阅读又能用膳的开放书屋;数间厢房,装修成饮茶或喝咖啡的,供几人私语。
我对建筑很无知,审美缺乏核心视角。孰优孰劣,纯粹就是感性直观。
“中轴对称,严谨守中”,这是专家的房屋建构模式说。平衡稳定加和谐统一,是老祖宗文化中的一层意识与讲究。开敞的院落、回廊、厅堂彼此呼应,与接日纳雨的天井融为一体。类似这样的居住空间,能够张张嘴就购置下来做恒产的,也惟先前那些富贵兴旺起来的家族可为。也许那时候,再大的私产都只能是私有,国家也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台阶、门框、花座,文字、雕刻、绘画亦新亦旧,旧瓶装新酒。和这些天所到过的其他院落一样,种种清晰与模糊,勾兑呈现着不无复杂的属性,一片朝代被更替人间被置换的痕迹。东张西望后,踏实在其间定睛了几处。只是,面对改造的书店我一无所获。绕来绕去,还因燥热不散,一次赏心悦目的感觉也始终未现。
上楼喝茶,和朋友们开聊。
想起之前在郎官巷喝茶。据朋友说,作为大人物和读书人的严复,返乡消沉间,老先生居然还想再考出个“举人”来,以其功名弥补中学的缺憾!虽满腹经纶、学贯中西,自己的学识与皇皇译著也早为朝野上下所仰慕;其名声、贡献也绝不亚于朝廷上唯唯诺诺的李中堂。似乎,这也类似时下热闹的官员考文凭,拾遗补缺。但严氏绝不虚荣,更非鸡贼,而是要奔向完美的执着。1900年,严复在英国就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那时候,他已了解“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的现象。并理解:国家与个人,权力与权利,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公民自由与社会进步的文明关系。仔细想想,那得要求一个人是多么地睿智和“先锋”才行!
在晚清社会,没人能像他那样洞察了这个国家文化与思想动力的匮乏。居然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认为应该“体用一致”,并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现代教育思想。从福州出去的历史人物中,严复的深度思考无疑位居巅峰。
但是,我没发现书架上有严复的图文。或者,在这个国家的历史陈述中,至今为止,似乎也没能讲明白:严复之于现实,其思想真正的价值究竟何在?
伟大的严复,似乎无数次地复活过。但其魂,却迟迟未归。
回头看,那个所谓“书局”,大概无局可言,即便靠简餐与卖书混搭似乎也不太靠谱。老板年轻有理想,感觉有点飞蛾扑火。大门之外,巷子深深而人心惶惶,要仰仗历史的文化碎片,来砸醒疲软的当下阅读兴趣,吸引已慵懒失志的涣散人群不为难吗?求生越加物质化,人们涌向茫茫人海,以捕鱼心态尝试收获。
那即点即享的海量抖音,也早就成了折损“精神贵族”的强大对手。“新东方”都重新带货上路了,生存的方式方向漏出了偏颇。朋友一家高档酒吧撑不住,数天前在三坊七巷中轰然倒闭。令人担忧的病毒,失业潮,中产阶级……
毕竟,这不是一个读书人的时代。
30平米咖啡馆。据说,咖啡诞生时并不高贵,不过是一个牧羊人对“羊的兴奋”的发现。后来是士兵的兴奋剂,再是病人的麻醉品。人类的精神需求,一步步改变了它的身份轨迹,使其成为现代人上品的生活方式。或许,有了发育良好的草根阶层,社会文明才有指望?
似乎,三人要准备借用这优雅僻静,或新或旧开辟新话题,也装一回有品位的文人墨客。巧在外头天空显出一副忧郁的灰,室内的颜色渐变,混合着并不强烈的灯光,介于某种冲突又和谐的矛盾氛围正被营造出来。这是“三坊”之一光禄坊的一间清代旧址。有记载,因福州郡守程师孟吟过“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一诗,“光禄坊”便由此而得名。官员有文化,风景多乎哉?
三坊七巷的故事多得难以计数。一石一木,一砖一瓦,或都能抠出如歌如泣、荡气回肠的过往历史。可惜,历史又不能为自己做主,往往能留住并往下流传的,大多都是被各式爱好取舍、剪辑的结果。尤其那些悠关人类命运是非的秘密,因为统治者的忌讳,一代一代,都被遮蔽或封存而秘而不宣。
这间房,一直半明半暗着。我们不知它曾拥有过什么。但此刻,窗外云层经过多次叠加,浓稠得不见云色。风雨欲来,也很容易在人的心间扒开缝隙,挤进某种突然的记忆——那些大时代里大同小异的故事或事故。
二
咖啡端上来时,一股香气让我首先想到了咖啡因。可这下,却让思绪跑得老远。定格后却成了这样:某个衰败的家庭,一个失意的书生,是否就在这里,或比此时更晚一点,日落西山,屋里没多少可以探物的光线。他不是端坐在椅上而是斜躺在床上,正抽着一袋又一袋的鸦片,诅咒着某个朝廷的某个皇上或某个朝臣:以古人的思路,折腾着今人的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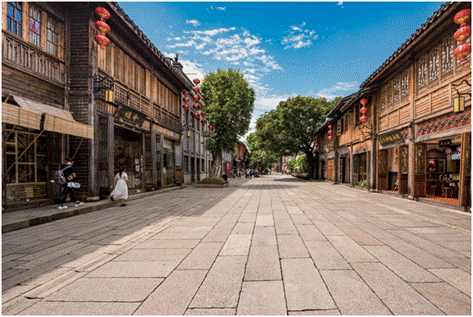
三坊七巷
曾经,随着一次次“城头变换大王旗”,三坊七巷中贵族大小户们无不闻风而动,各式应对。或家或国,忽兴忽亡,谁也无从预先安排好自己的命运。变革者如林旭择同归于尽,革命者如林觉民却义尽身舍,探索者如严复欲启蒙未果,爱国者如林则徐因制夷流放,求真者如林白水为自由就义;而强军者如萨镇冰则屡败屡战——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动荡进程中角色各扮、精彩各抒;而人非神仙,尺短寸长,也彰显出个人对历史顽疾的片片无奈。
作为具有“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声名的所在,大概其中更多的人经不起各种风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起码,那些显赫一时的家族纷纷覆灭,也包括散落在乡村世界的富裕阶层。在中国,所有胜利的政权几乎都喜欢剥夺有产者,而坚持忽略绝大多数的有产者都是来自无产者,以及他们曾经的挣扎、艰辛与摆脱。
民间社会,走向衰微的欲望,是三坊七巷终结的开始。
还有斩草除根,赶出田庄与家园,让他们失去个人的历史记忆,想不起自己从哪来到哪去。处在永久彷徨中的人们,由于易生绝望而麻木,最终就难免如无根无力的稻草,或遭捆绑,或被放逐。
我了解这里简单的变迁。而对三坊七巷的人物,却也能使自己产生出类似“梦牵魂绕”的情感。悲剧的、悲壮的,或是欢欣的、凄凉的,起起伏伏、深深浅浅,都打印在脑幕间。我曾以粗糙的文字叙述过福州,其间自有这坊巷的点点着墨,也算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风短雨长或风长雨短,那人物叠出、风流四起,事件云涌又变幻莫测的数百年,是怎样的一个天下,又是谁的历史呢?
不一会,已是昏暗的天空顿时向黑暗发力。几乎没人为此慌张、奔跑;天地之间像一场预演,默契如我。劈噗劈噗,雨点开始敲打着玻璃墙面,墙外繁茂的树叶七扭八歪。紧接着稀里哗啦,大雨向下俯冲,急速地渗透入热气嚣张的大地。高高的屋顶,矮矮的花盆,路人的脚上,河道的水面全是它的潇洒。
这天上的雨,果然来了!
抬头望,树梢挂着半颗被切开的金色石榴,如无影灯闪闪发亮,那是玻璃自己玩出的一层意境。水,在一块青石板上,不断地跳舞,姿态多变;它不同的节奏和韵律,同周边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关系。我凝视着、放大着,想象过往的数百年——不仅这一角落,也不局限这一细节,而是整个三坊七巷和它的天翻地覆。
这雨,即便重逢却还陌生。

林旭
我离开福州20多年了,划出来的距离,也可以放下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比如林旭,那位和谭嗣同们一起行变法的戊戌君子,那时才23岁!某日在塔巷,福州知名剧作家林瑞武先生告诉我:林旭的后事非常悲惨,他被砍了头的遗体运回老家,却遭到唾骂;那些乡亲用铁钎强戳他的灵柩,也许穿过了他的身体。闽剧《银筝断》,是林先生为纪念林旭所撰。
在京城的这些漫长岁月,我也没敢忘却他们。
那个鲜血早被各种冲刷洗尽的菜市口,每当路过,胸口也会突然涌上一种痛。
听雨,要听出失去的神韵;看雨,也试图要看到归来的神情。身在别处,不同的世态,难以确信与验证一种凄风苦雨乃至泪如雨注的比喻,也推敲不了这边由山水互动的人间,或因现实而超脱成一种闲适、泰然或偶成麻木的语境。
三
雨在继续下,覆盖了三坊七巷。淅沥雨点,混合脑中释放的情节,正如一卷转动的电影磁带在缓缓迟行。窗外,男男女女撑伞的行人。经过一辆人力清洁车,绿色的车斗,湿漉漉的车轮,看不清雨衣里的蹬车人。
挨我最近,一个年轻人,隔着玻璃,坐在屋外属于咖啡店的延伸区。再往身后,似乎就是那条“中国最短”的文藻河了。一把硕大的遮阳伞,女子在下面,任凭豆大密急的雨点在头上敲击。雨从瓢泼到倾盆,之后慢慢收敛。她身着有点暴露的低领上衣,一袭长发垂在胸前。抽着香烟,一边若无其事又若有所思。
一时间,钩来了林徽因、谢婉莹以及庐隐的身影。故乡若即若离,但她们却根源于此。我无法猜断,对面的女子是否也有另类的风骨,或守着时代的庸常度日如年?这般朦胧的雨境,形象变得重叠又破碎。不时,那曾忧郁、沉思与叛逆的历史又依稀浮现。特立独行的个性,跳不出时间的印痕:这些才女的精神之花开放在民国。
忽然想起了梁实秋先生。某年到台湾,走访了故居。那天台北也下雨。一间理想的“雅舍”,布置得真是雅致,温馨,轻奢。虽在夜间,主人早已故去,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与外部人生的关系,他所热爱的那般生命与那缕光明。那屋外的一片景致,与我此刻所处的情形相近:木栅栏围着小小的庭院,四处滴滴答答;路灯下,雾雨迷蒙;树叶闪着一股清亮的光泽,空气中混合着一种无名的草香。
虽与台师大一步之遥,却能远离喧嚣,惟有文学和莎士比亚的陪伴。无论主人的生或死,这里都是文化的“雅舍”;不管外面的风和雨,里面全是温情的人性。
身为翻译家和文学家,他是民国的人,也有民国的魂。当年,大概鲁迅先生有自己对卢梭或别的捍卫,扣了梁先生一顶“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帽子;梁不服,回敬他自大得“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我猜想,应该是梁又借题发挥,将鲁迅与“卢布的赏赉”也拨在一起。这样的彼此刺激应该很出格,超越了文学,他们的撕裂便在所难免?
作为文人,他们还是自由地表达了自己。没人能为难他们作为观念与行为的独立存在。这似乎也是民国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
就在前些天,朋友带我去看了离这很近的郁达夫先生住居地:光禄坊的刘家大院28号。作家和妻子王映霞在此短暂生活过。据记载,正人君子梁实秋,最看不上眼的正是郁达夫,感觉他就是一个花天酒地、过于滥情的浪荡才子!大凡是人都有其多面性。只不过,多出的那一面人们不尽相同。包括这位郁才子在内,关键时刻却以大节弥补了小节,为民族尊严而舍生取义。

台北梁实秋故居
晚清与民国的许多文人或知识分子,不畏强权,铮铮傲骨,不失气节。他们之间可以观点对立,相互公开批评,甚至毫不留情地谩骂攻击,亏下私德。但却能够维护基本的公德,大仁不含糊;也可以一边过着穷酸的日子,一边继续为信仰殉道。他们几乎理解和遵从现代社会的常识,在各种主义间寻找个人价值依存的逻辑。拿博学明智的胡适先生为例,身体力行,以争个人自由,为国家争自由;以争个人人格,为国家争人格。
杯中的咖啡在逐渐下降。沙发上的三人,已失去了聊天的焦点。彼此身世不同、境遇各异,但同样都被绑定在这个年代,因而有了大体相近的文化与社会焦虑。比起从这里入世创造的那些先贤,作为后来者实在惭愧!至少我自己,一个俗人,几近苟活。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的确也怀疑许多存在,却包括了我自己。
对前人、对历史的真诚态度,决定了一个社会文明的尺度。
文化是最怕某种革命的,它会使激情澎湃中的人们摧毁人类柔弱的神经。那种由书籍、建筑构成的思想与人文的记忆,完全经不起任何政治的暴风骤雨。并且,在这个众多人物堆积的历史叙事间,隐藏着太多财富与社会、与人生的关系秘密。而其中,“私权不能公有,公权不能私有”,或许也是最值发掘与澄清的一种遗产?
四
三坊七巷,从专制到宪政,它是福州也是中国一个既迎接又告别的高贵群落。由高潮到落幕也终归是必然。不过,那是宦海沉浮、生离死别;那是秀才造反,义薄云天;那也是所有人之常情的求功成名,做大人生!而其间的文人与士大夫,他们曾经的风骨与精神消亡了吗?在这一座座陈旧的宅院府第里,除了用它往日的声誉、无形的阔绰,还有谁像淘宝一样,在刻骨珍爱或承继着此处的人类精髓?
每次踏进那一条条嵌满岁月的石板路,我就不禁要这样问。
经历过风起云涌、变幻不定的时代,那些看似正常实则怪诞的生活,都像一块块骨头,一根根神经植入体内,自行风干变形,剩下一点动静,成为精神意义上的活体标本。移动与展示是痛苦的,但也没有逃避或消解的通道。或许能做的,是以点滴的醒悟来拒绝梦幻。
而三坊七巷,属于另类而沉默的历史标本。
其实,我很不愿某种“同归于尽”的联想。时间过了傍晚,杯中咖啡随着雨歇见了底。
听雨,意犹未尽。
(作者为《影响力中国》杂志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