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陈镜清《朱熹首仕诗作笺释》
马照南
历时数载,潜心耕耘,陈镜清先生为探寻朱熹同安时期诗作的真谛,于资料匮乏中寻觅,在文献甄别里钻研,凭借深厚学养与不懈执着,终成《朱熹首仕诗作笺释》这部力作。此书专注于朱熹初仕同安主簿时期的诗作,为我们探寻这位大儒早年的心路历程与思想轨迹,打开了一扇珍贵的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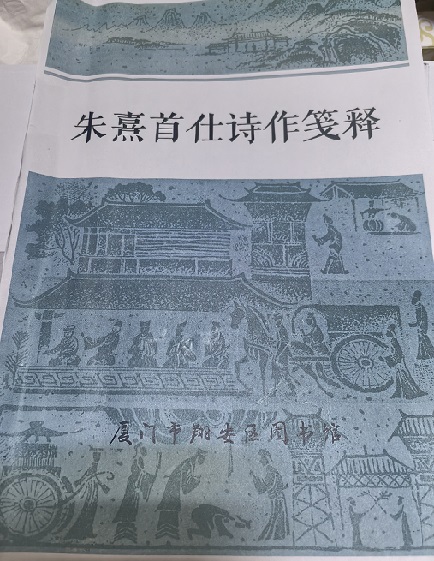
陈镜清《朱熹首仕诗作笺释》
朱熹,这位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巨匠,其任同安主簿四年意义非凡。这四年被视为朱熹政治、学术乃至人格定型的关键阶段,历来评价极高。我们通常说,朱子思想融汇了儒释道,成为集大成者。这个过程,很大一部分是在同安完成的。有学者形象称之为“逃禅归儒”,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融禅归儒”。在同安,他完成了由佛老之学向正统儒学的彻底转向,更坚定了新儒学,即理学体系的价值底色,而这四年正是他后续完整理学体系构建的起点。他的爱国为民政治理念趋向成熟。初仕时,他面临的是县学衰败、科举空疏、民风杂糅。他把理学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理想付诸实践,也体会到“义理”必须落到“事功”。他以“视民如伤”为念,把“恤民、教民、治民”融为一体,整顿赋役、盐政,试办社仓,减轻百姓负担,做了许多好事。
后世评价他在同安的贡献。一是教育奠基。重修孔庙、尊经阁,新建九日山、小山丛竹等多所书院,订立学规五条(五教、为学、修身、处事、接物),把散漫的县学变成“海滨邹鲁”。亲自授课、延聘名儒,扭转“专意科举、不究义理”的风气,使同安成为闽学首兴之地。二是治理典范。“政教合一、以德为本”的治理范式,开“闽学教育模式”和“朱子治体”之先河。青年朱子“莅职勤敏,纤悉必亲”,县中狱讼、赋役、祠庙修缮,皆亲为裁决;为民办一事、不避劳怨。首倡修《苏丞相正简祠堂》,借先贤廉德化民成俗,开同安“清官文化”先河。三是使同安成为朱子学重要发祥地。800多年间书院屡废屡兴,代有官绅修复,之胜在同。”言下把闽南人文鼎盛首推朱熹之功。
朱熹13岁就写诗。《朱熹集》卷一“少作”共17首,内容多为题寺、咏物、写山水小景。其父亲朱松亦以诗文名世。他在《跋韦斋示儿诗后》中记:“吾儿元晦,年未弱冠,诗语清婉有思致”。朱子创作数量多、时间久,有存诗1200~1300首,50余年几乎没有间断。被誉为是理学圈“首席诗人”。钱钟书称其“道学家中的大诗人”,清人李重华更把他与陆游并列为“南宋两大家”。
朱熹诗歌之所以能在“诗人林立”的南宋别树一帜,关键在于他把“理学体系”完整地、成规模地转化为诗歌的“创作语法”。一是把“格物一致知一豁然贯通”的工夫论写成诗的结构。传统山水诗多为“起一承一转一合”的情绪或画面铺陈,朱熹则把“即物穷理→反复涵泳→一旦豁然”的三段工夫,外化为诗的三段式:取景(格物)→疑思(致知)→透悟(贯通)。如《观书有感》先写方塘、天光,次写“问渠那得清如许”,末句点破“源头活水”,恰是“豁然贯通”的瞬间,形成理学诗独有的“认知一审美一悟道”同步完成的结构;二是系统打造“理学意象群”。他高频使用“源头活水、半亩方塘、万紫千红、云谷月窗、书灯雪屋”等意象,并赋予固定哲学语义,成为可不断重释的“理学符号库”。如《春日》中“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春”,象征着万物生长、天理流行的美好境界。其后学王阳明、曾国藩等人写“致良知”“格物诗”,均直接沿用这一套意象;三是让“议论”成为诗中最具张力的“抒情”。朱熹用“理语”取代“情语”,并保持诗的声律美和跳跃感。如“只此眼前都是易,何须别处觅先天”(《易二首》之一),一句议论,却用对仗、顶针、双关,形成“理趣的骤转”,把哲学命题变成了“警策式抒情”;四是把“日常讲学场景”变成诗的母题。他把“夜读、课徒、会讲、书斋静坐”这些理学家最普通的日常,化为诗材,使“讲学”本身成为一种可审美的生活形态。如《牧斋净稿》大量“灯下读易”“晨起课儿”诗,开创了“学者生活诗”传统;五是以“群体唱和”方式传播理学诗学。朱熹在武夷精舍、云谷草堂、白鹿洞书院等组织弟子同题共咏,形成“理学诗社”。这些唱和诗并非应酬,而是围绕“中和、性情、主敬”等主题展开“诗化讨论”,等于把诗会变成了“流动的课堂”。此种“以诗讲学”模式,被朝鲜李退溪《陶山杂咏》、日本藤原惺窝《倭京百咏》直接移植。他注重“理趣”,用诗的形式完成了理学世界观的审美转化,从而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朱子风格”。
朱熹在同安期间的诗作,反映了其彼时生活与思想的鲜活印记。《宿山寺闻蝉作》《宿白芒畲》等诗作中,山寺、蝉鸣、山野居所等意象,既体现了他访仙问道的经历,也流露出他在世俗生活之外寻求精神慰藉的心态。蝉鸣在寂静的山寺中,既有自然的清幽,也可能暗含着他内心的孤寂与彷徨,而宿于白芒畲这样的地方,则显示出他在生活奔波中的一种漂泊感。
《池上示同游者》《过黄塘岭》等与游历相关的诗作,既记录了他的行迹,也在与同游者的互动或途中的所见所感中,展现出他复杂的心境。池上的景致或许让他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与同游者的交流也带来片刻的欢愉,但过黄塘岭的路途艰辛,又可能让他联想到人生的坎坷与不易。折射出他待阙时生计窘迫的哀愁与对未来的迷茫,那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在诗句间流转。《新竹》一诗,新竹的蓬勃生长可能象征着他内心对未来的期许,即便身处困境,仍充满对生命力量与希望的感知,而新竹的坚韧也暗合了朱子坚强性格。
我与陈镜清老先生相识多年,得益甚多。他是记者也是教师,更是我省著名的徐霞客研究专家。他对朱子诗歌的研究,缘于1994年中国旅游学会山水旅游文化委员会在深圳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在会议期间与厦门大学蔡厚示教授谈起了福建省山水旅游文化资源。蔡教授论及朱熹的“纪游诗”的文学创作及对福建省发展山水文化旅游的价值。由此引发对朱子诗歌创作兴趣,萌生研究朱子文化及其诗歌的意向。此后在《闽南日报》主编“文化走廊”“社会大观”等专版,时不时引用“朱子守漳”历史政绩撰写评论,时而刊发朱子诗作笺释,颇受读者欢迎,起到了很好的朱子文化传承及宣传效果。
21世纪初,作者告别记者生涯,重操教师旧业,潜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他常感朱子文化博大精深,传承之责重于泰山,遂参与创建“北溪书院”,将“朱子及陈淳诗作”列为教材。又与著名朱子学研究学者何乃川教授交流,并获赠何教授专著《闽学困知录》,在何教授的启发与指导下,更坚定了研究朱熹在同安思想转变的决心,萌生笺释朱子首宦同安诗作的想法。接手此项工作后,他花费多年心血,四处搜集资料,反复考证,终于在翔安区图书馆大力扶持下,专著由鹭江出版社正式出版。陈镜清先生对这些诗作的精心笺释,不仅深入解读了诗作的内涵,更结合历史背景与朱熹的经历,为我们厘清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这对于学界重新审视朱子主簿同安时期在其整个学术发展历程上的意义,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相信这部《朱熹首仕诗作笺释》的问世,必将为朱熹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为众多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坚实的参考,助力我们更清晰地探寻这位大儒思想的成长轨迹。
是为序。
写于2025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