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平《何振岱年谱》序
陈庆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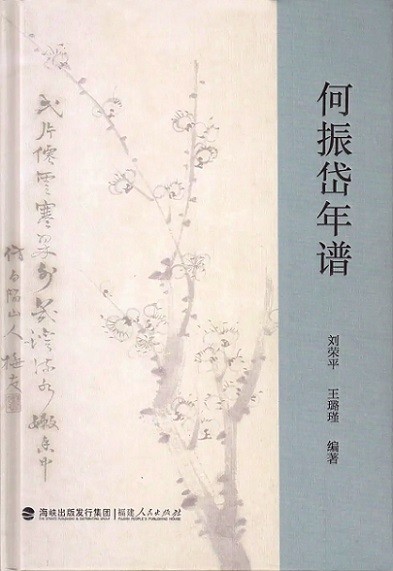
《何振岱年谱》是刘荣平教授继《福建词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之后的又一部新著,合作者为王璐瑾。
何振岱(1867—1952)、李宣龚(1876—1952)是两位闽中诗人,三十多年前本人撰写《论同光派闽派》(《诗词研究论集》,巴蜀书社,1998年)长文将其合为一节,称“同光体闽派殿军”。其时,暨南大学毛庆琦教授编《近代诗歌鉴赏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约我撰稿六篇,其中何振岱两篇,篇目自选,我选了《疏雨》和《瑞岩》。2000年前后,我先后参加十数种鉴赏辞典撰写,朝代由先秦到晚清,每写一家,必找原集阅读,虽然很费时间,却多少弥补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功课荒疏造成的知识缺陷,扩大了知识面。差不多也在这一时段,陆续有青年教师跟我进修,我让他们分别研究一个福建近代作家,如梁章钜、陈宝琛、陈衍、何振岱等,还有一个硕士生选李宣龚作为毕业论文。闽江学院刘建萍老师做的研究就是何振岱。建萍报考博士,名额有限,改换到其他教授名下,研究方向也随之改变,觉得有点可惜。荣平博后出站报告研究的是谢章铤与聚红词榭,何振岱为谢章铤及门弟子,不仅工诗,且工词,故请荣平一并关注何振岱。荣平将此事放在心上,开始广搜何振岱文献,并陆陆续续发表何振岱的论文十来篇,形成系列。二十年后,2024年冬,荣平说《何振岱年谱》已经告竣,即将付梓,请为序弁其端。
年谱是一种特殊的传记体著作或作品,它逐年甚至精细到月、日,载述谱主一生经历的事件、活动、交游、言论;如果是作家或诗人,还要为他的著作、诗文系年、系地。年谱著作,引证必须详尽、准确,间有简明扼要的按语、阐发。一部优秀的年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谱主作为撰著对象至少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某一方面意义;“反面”人物有时也有“反面”的意义。其二,有足够的传世文献资料支撑年谱,而且撰谱者能够详细占有它。南宋诗人萧德藻,福建闽清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杨万里称“四诗翁”,有《千岩择稿》七卷,已佚,可考事迹寥寥,这属于文献不足、作不了年谱一类;有些谱主传世文献明明有足够多,但是撰谱者没有用心搜集,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充分掌握,撰谱工作也很难进行。其三,撰谱者必须具备敏锐的史识眼光,能够运用好手头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辨分析,对史实、诗文作品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何振岱年谱》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年谱。何振岱是同光体重要诗人、书画家、古琴家,一生横跨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何振岱三十一岁成举人;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时,何振岱已经四十五岁,诗名满天下。同光诗人同是学宋,闽人清苍幽峭,赣、浙生涩奥衍。何振岱则以清净、冲澹、富见神理见长,在晚清闽人中自成一家。中国文学研究重视分期分段研究,必有它的道理。一般认为同光体是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的一种诗体,按照文学史的分期,属于近代文学史的范畴。但是,同光体闽派主要诗人陈宝琛(1848—1935)、陈衍(1856—1937)、沈瑜庆(1858—1918)、郑孝胥(1860—1938)等,一直活到民国。二陈、沈、郑之后,何振岱、李宣龚吟咏不辍,同光诗体的薪火不因时代更迭而寝熄,一直延续至1949年之后。了解何振岱、李宣龚一生的诗歌创作经历,对我们研究清同治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这个诗歌流派的续存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就生命个体而言,何振岱和李宣龚1952年就去世了,何、李去世后,同光体闽派似乎可以宣告彻底结束了。文学发展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文学流派的结束并不完全与它的代表人物去世的那一天、那一年同步,可能还将延宕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时期,因为他的弟子、门生还在,影响力还在。何振岱的及门弟子尤其多,女弟子刘蘅(1895—1998)一直活到世纪之交。近代以来,福州得风气之先,二十世纪初,办女学,男女同校,女性走出家门,何振岱的女弟子成了近现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风景。研究何振岱诗歌近现代的传承,尤其是传授女弟子的过程及其得失,对研究近现代的诗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何振岱的人品很值得称道。何振岱富有民族气节。抗战爆发,福州沦陷,日人慕何振岱之名,拟聘为顾问,遭严词拒绝。随后,何振岱把同沦为汉奸的郑孝胥等人的来往信件焚毁,以示决绝。他的学生中有一批爱国志士,吴石(1894—1950)便是受何氏影响较深的一位。吴石终生不忘其师,在被派往台湾领导地下党工作前夕还专程拜望老师,后来在台湾慷慨就义。
何振岱的传世文献资料较多,足以支撑编写一部比较完整的年谱。荣平教授千方百计,以足够的耐心去寻访、搜集,详细占有这些文献资料。荣平教授不是第一个把何振岱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的学者。此前,刘建萍博士已经出版过《诗人何振岱评传》(2004),点校《何振岱集》(2009),还访问过何氏后人,搜集到部分稀见文献;201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还影印《何振岱日记》。尽管如此,何振岱还有许多文献资料未被发掘、使用,荣平教授不辞辛苦,百般求索,他获得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四方面:其一,扩大阅读面、搜集面。凡与何振岱有交游的人物资料,能找尽找,能读尽读。其二,动手抄录。图书馆藏书不是所有书籍资料都可以借出来影印或拍照的,荣平教授经常往返于福厦,住客栈,白天到图书馆抄书,晚上读之,乐此不疲。其三,放低身段,联系何振岱后人、门生,能要就要,要不到就拍照、抄录。其四,荣平人缘好,学界朋友知其为学问中人,往往倾囊中何氏资料馈赠,不吝也。因此,这部《何振岱年谱》引述不少非常罕见甚至是海内外孤品的资料,如油印本、稿本、讲稿、尺牍、抄本、抄件、拓本、扇面、题辞等,让读者耳目一新。
荣平教授具备敏锐的史识眼光。图书四部分类法,年谱属史部谱牒类。一般说来,谱主都是过往人物,时代或远或近,都是历史人物。和其他撰史者一样,撰谱也需要具备史识。荣平教授对本谱撰著的设计,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称道。首先是注意何振岱亲友、弟子和谱主的交集。年谱撰著,谱主当然是主轴,是主干,但是每一个社会人都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亲属(长辈、同辈、后辈)中间,都不断地与各个时期的师友、同事、同僚、弟子来往。如果一部年谱缺少谱主亲属、师友、同事、同僚、弟子的载述,这部年谱必然是平面的、单线的,而不是立体的、网状的。荣平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整部年谱征引了数十人的事迹、著述,重要的就有十几二十人。其次是“谱前”“谱后”的设计。何振岱1952年谢世,如果年谱安排到这一年而止,也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处理,就看不到何振岱的影响,看不到同光体闽派在1952年之后的延续,也看不到何氏去世后社会对他的尊重和推崇,看不到后世对他的著作的重视,因此也会影响到对他的评价。本谱的叙事,一直持续到2018年闽江学院举办何振岱研讨会,给人留下连绵不绝的袅袅余音。何振岱与陈衍晚年交恶,是本谱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荣平教授征引翔实的资料加以考察,认为是何振岱性格上的狷介寡合使然。这一判断,应当较为接近史实。在具体事件方面,寿香社于十九世纪末创立,这是何振岱一生组织过的最重要的诗社,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达百年。荣平教授对其成员及活动考证缜密。
王璐瑾是荣平教授《何振岱年谱》的合作者。荣平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书,王璐瑾是本科生,荣平是她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荣平给她《何振岱年谱》这样一个题目,并把所藏的何振岱文献资料都给了她,精心指导,给她信心。我很欣赏荣平教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术的大海中遨游,激励她,引导她,教她以方法,提供文献资料的协助。《何振岱年谱》的成功,还在于师生的合作,教学相长。这也是我特别推崇《何振岱年谱》出版的原因之一吧。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3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