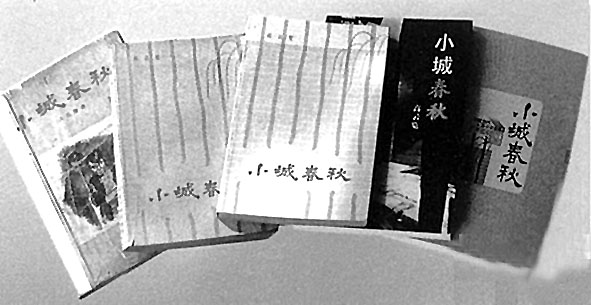风雨平生忆云览

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人们被从四面八方推上一个浪峰,从互不相识到成为朋友,是常有的事。1936年,高云览在厦门中华中学教书,经常在厦门《江声报》发表文章。我在厦门《星光日报》当记者,写不署名的新闻,也写署名的特写和小品。他的学生中,有几位我熟悉的青年,时常用钦敬的口吻谈起这位老师。我知道他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书名《前夜》,笔名健尼。因此,对他有了印象。
其后,我们在文化界的一些集会上相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相识而且成为朋友。这位相貌清秀,谈吐文雅,具有知识分子特有气质的青年教师,比我只大5岁,而在文学素养、待人接物各方面都显得成熟和老练。他和当时许多文化界青年一样,对于抗日救国有颗炽热的心。
因为大家都忙着,我和高云览过往不多,不常见面,偶而相逢,由于思想情趣上的某些共通,诸如对文学的爱好,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丑恶现实的诅咒,倒也话语投机,很谈得来。见面地点往往是在厦门闹市思明南路一家咖啡店。这里有钱人不愿来,三餐不继的穷人无法进。在当时,边喝咖啡边发一些不着边际的议论,是被认为颇富诗意的,因而它是文化人聚会的好处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厦门地下党筹备组织鲁迅先生追悼会。当时是“西安事变”前夕。白色恐怖仍很严重。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了使追悼会不被扼杀于筹备过程中,而且努力争取把大会开好,筹备工作开始是秘密进行的。待到酝酿成熟,成立筹备委员会,才进入半公开状态。在最后的筹委会上,决定邀请高云览担任大会主席,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我是在党影响下的一个小青年,没有参加最初的筹组工作,许多情况不了解。70多年后的今天,在回忆鲁迅追悼会的筹备历程和高云览担任大会主席的经过时,一开始就参与筹备工作的曾克里为我提供了当时的情况。这个组织的开始及至最后大会的召开,是在当时厦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最初几个人是党的负责人尹林平、肖林以及党的外围组织《实艺社》成员曾克里、胡一川、郑书祥、鲁默、柳青、陈义生等。其后分头进行联系与动员,交换意见,取得步调和意见的一致。先后有林东山、童晴岚、马寒冰、许印滴、赵家欣参加,正式成立筹委会。大会决定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筹委会研究大会主席的人选,筹委中有的不便出头露面,有的社会声望不够,大家想到高云览,认为他是比较适当的人选。高云览热爱和崇敬鲁迅,经常向学生推荐鲁迅作品,向学生介绍自己名叫高法鲁;他是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平时不大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他担任追悼会主席,大会的举行可能较少风险。通过当时《江声报》编辑、在中华中学兼课的许印滴出面邀请,高云览同志慨然担任了追悼大会主席,而且鼓励他的学生参加追悼会。11月29日9时许,已告满座,乐队奏歌开会。高云览组织的学生歌咏队唱起《哀悼鲁迅先生》的挽歌。挽歌二首,其一是:
天空里陨落了一颗巨星,
黑暗中熄灭了一盏明灯,
去了,永远地去了,
你一代的文豪!
像孩提没有了慈母,
像夜行失去了向导,
千万人都在同声哀悼,
从此我们只好擦干眼泪,
踏着您光荣的足印向前跑。
伟大的死者哟,
您的名字已经变成后来者的路标。
另一首悼歌是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谱唱的: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争生存!
他反抗帝国主义,
他反抗黑暗势力。
一生到老志不屈,
始终为着革命而努力!
哀掉鲁迅先生,
哀掉鲁迅先生,
———我们的导师!
歌声从低沉到高昂,从歌咏队到全场大合唱。歌声使人群似潮的会场增添了激越悲壮的气氛。继而由总主席高云览代表主席团致词,他很沉痛地说:“……先生(指鲁迅)不单是一个反抗黑暗势力的正义作家,而且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敢的战士,我们追悼他,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他的遗志,继承他的精神,让帝国主义从华北滚出去,从东四省滚出去,这一场追悼会的意义才不会落空,而先生在地下,才不会不瞑目了。”当年故友马寒冰(历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处副处长、文联副主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写了一篇题为《伟大的民众祭》的报道,刊于当年《闽南文艺协会会报》。其后被收入鲁迅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出版。在这篇具有历史性文献里,报道了“伟大的悲壮的民众祭”的实况,并记录下高云览同志的开会词。“厦门市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得以胜利召开,高云览同志是尽了一份力量的。其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虽然默许召开这个三百多人参加的隆重追悼大会,但鹰犬们仍虎视眈眈,暗地四处监视。高云览同志讲话有如利剑出鞘,直刺向国民党反动当局,更引起特务们忌恨。果然不久,中华中学校长、国民党复兴社头目王连元对高云览施加压力,高云览同志被追不得不于1937年春离开厦门,流亡异国他乡。
临别匆匆,我和高云览又一次在咖啡店会晤。他告诉我,他将要离乡南渡,前赴星洲。前些时日,云览为了失去名叫喜鹊的年轻伴侣而忧郁感伤,沉默寡言。这次他是要和我话别了。对于他家庭的变故,我无语慰藉;对于他将要去国远行,我是颇有惜别之感的。我已记不起来当时在默然相对中说了些什么话,但我记得在互道珍重时,在纪念册上互题了黯然神伤的送别词。云览写的是李商隐《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写的是王维《渭城曲》: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咖啡当酒,淡淡离愁。在这个咖啡店内,我怀着惜别的心情,送走一个个远离苦难祖国,飘洋渡海,走向异邦的朋友。不久,抗战军兴,烽火漫燃,故土沦丧,我奔波流离,历尽艰辛。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蹉跎,对于海天遥阻,寄身海外的青年伙伴们,思念之情也就淡漠了。
在抗日战争到祖国解放后的漫长岁月里,从青年老师、爱国华侨到革命作家的高云览在海外和回国后的所有经历,我是直到他逝世后才从一些纪念文章中看到的。这是由于解放前后,我长期滞留他乡,没有重返家园,经历多年离乱,抗日战争前后在厦门分别的朋友不知我的存亡;他们的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我也没有去探问。直至今天,不少寄身海外的朋友仍然未通音信。
1956年,我因事回到厦门,高云览同志在海外结识的好友、当时担任厦门市副市长的张楚琨同志给了我一部《小城春秋》油印本,征求修改意见。我才知道云览早已回到天津定居。1957年初,我再度赴京,在天津停留探望朋友,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孟秋江同志告诉我,云览已于一年前病故。这一噩耗,使得厦门咖啡店分别时的情景,在已淡漠了的记忆中重新浮现。我和云览虽然相处的时日无多,交谊也不算深厚,但青年时代声气相通的朋友,印象一直是鲜明的。
于是,我珍藏着《小春春秋》油印本,小说出版后,我又买了铅印本。张楚琨同志的序言,高云览同志的“写作经过”,都在说明小说是云览一生心血的结晶。我喜爱这本书,不仅是出于“爱屋及乌”,为了纪念早逝的朋友;更多是小说叙述的这个革命故事发生在我的家乡,书中的人物大多似曾相识,不时勾起我青少年时期某些朦胧的回忆。中学时代那位被国民党押送省城而死难的聪明沉着的“大同学”,初当记者时期那位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的才气洋溢的“老同行”,还有那位幸免于难,别妇抛雏,远走天涯海角,杳无音信的温文尔雅、热情似火的年轻诗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未来,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我无法忘却这些革命者的形象,但我没有能力用文学去表达他们的壮烈事迹。高云览同志是个有心人,他几乎是用毕生精力,锲而不舍地从事这一极有意义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以厦门大劫狱为题材,把英雄们的光辉形象通过生动的笔触映现在小说中,使他们栩栩如生。小说体现了革命年代一幅历史的画面,谱写了一曲激动心弦的壮歌。这个画卷,这一乐曲,将会激发人们对同一历史时期,没有在书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为革命献身的英烈们的怀念。小说的结局为革命留下了火种,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作者意义深长的用心,他如实地体现了革命斗争的挫折和胜利,因而更加激奋人心。
时光倥偬,高云览同志逝世不觉已过半世纪了,我也进入年过九旬的暮年,但他的形象仍长存在我记忆里,我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小城春秋》及一系列遗著,至今仍在广大读者中流传。当前,面临文化改革大潮,继承发扬先辈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谱写新曲,是后继者的职责。他的女儿高迅莹编的这本《高云览纪念文集》,学术性、史料性,兼而有之,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高云览及其著作,人们可以从中学习取得借鉴。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我乐于向读者推荐。
二○一二年十一月
于福州南方温泉公寓 时年九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