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在海中”二重证据考
汪征鲁
关于福建先民的产生与演化,我涉猎了许多的文献及考古发掘报告,也陆续写了若干杂记,其梗概大致为非洲智人之南来——闽在海中——七闽——闽越国——中原人南渐,将在以下的“汪汪夜读”中娓娓道来。据人类细胞线粒体 DNA 的研究,非洲智人为全球人类最早的祖先,当是大概率的事实,然其如何辗转入国中及福建,还有许多缺环,这里先谈“闽在海中”。
一、“闽在海中”文献考释
(一)《山海经》“闽在海中”注疏
先秦文献称最早的福建居民为“闽”,亦可称为闽族。“闽”后又转化为地名。《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其意为:“闽族生活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说闽族生活区域中的山也在海中。”
后世对《山海经》的训诂首推清代吴任臣(1632—1689)的《山海经广注》、郝懿行(1757—1825)的《山海经笺注》、毕沅(1730— 1797)的《山海经新校正》和今人袁珂(1916—2001)的《山海经校注》。
对前文,袁珂作了两处集解:一释“闽在海中”,引郝懿行云:“建安郡故秦闽中郡,见《晋书•地理志》。《汉书•惠帝纪》:‘二年,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颜师古注云:‘即今泉州是其地也。’”“珂案:此泉州即今福建省福州。”我以为,郝懿行注解的:闽为建安郡、闽中郡,不确。所谓“其西北有山”,系指闽族生活区域的西北方向有山,此为福建的内陆地区,也就是秦时闽中郡、三国东吴的建安郡之大部分地区。唐人颜师古注解为泉州,唐代一度称后来的福州地区为泉州,故袁珂认可。我以为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当更恰当。一释“闽中山在海中”,引吴任臣云:“何乔远《闽书》曰:‘按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有穿井辟地,多得螺蚌壳、败槎,知洪荒之世,其山尽在海中,后人乃先后填筑之也。’”其意为:“所谓海中,是指今天挖井开地时,每每挖出海螺、海蚌外壳、朽坏的木筏,可知远古时代,这里的山都是在海中,现在的陆地是后人填筑起来的。”[1] 我以为,远古时代福州地区东南诸山均在海中不错,而现在的陆地是后人填筑起来的则不然。这在后面将详论。
(二)《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作者考释
上述的集解虽阐释了若干字面上的意思,但并未确指“闽”是什么人?他们处于什么时代?这就要先追究《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对此,历代学人做了不懈的研究。
《山海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其意为:“《禹本纪》记载:‘大河源出昆仑山……’……所以言及九州山川,《尚书》的内容还比较真实,至于《禹本记》《山海经》所讲到的怪物,我不太相信。”《禹本记》现已遗失,但司马迁是看到过《禹本记》。据我看来,司马迁至少认为,《禹本记》《山海经》及《尚书》的若干内容或出于禹夏时代,或反映了禹夏时代信息。
汉代学者大多主张夏初的伯益撰《山海经》,即夏朝初成书说。如前面提到的西汉司马迁即有《禹本纪》《山海经》为同时之书。
东晋郭璞谓西汉刘秀(即刘歆)亦主此说。其云:“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雠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2] 其意为:“为官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的臣下刘秀,主持秘书省的校书、校雠工作。太常属官望所校的《山海经》,共三十二篇,今定稿为十八篇。已定稿的《山海经》产生于尧舜以后……大禹划分了九州,依据土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而伯益等区别事物的善恶,著《山海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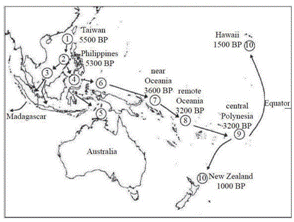
澳大利亚学者贝尔伍德提出的
“南岛语族”在太平洋岛屿上的迁徙与
扩散路径的 “Express—Train”( 快车 ) 模型
东汉王充谓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3] 其意为:“禹和伯益共同治理洪水,禹主持治水,伯益负责记录异常之物,海外山里,无远不至,以其所闻所见编纂了《山海经》。”
东汉赵晔谓:“(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4] 其意为:“禹于是巡察了长江、黄河、济水、淮河四条入海的河流,与益、夔共同谋划。巡视到名山大湖,就召见当地的神仙而向他们询问山河的脉络条理、所蕴藏的金银宝玉、生活于此的鸟兽昆虫种类,以及四面八方的民族习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拥有的土地里数,都让益分别记录下来,所以结成一书取名为《山海经》。”
由于,夏初成书说缺乏坚强的证据,宋、明以降学者多持战国成书说。明人胡应麟谓: “《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刘歆谓夏后伯翳(益)撰。无论其事即其文与典谟、禹贡迥不类也。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5]其意为:“《山海经》是古今以来神怪著述之祖。刘歆说是夏朝伯益撰写的。其无论所记之事和文风与《尚书》《禹贡》都不同。我曾怀疑是战国好奇之士依据《穆天子传》的内容与文风并将之扩充、提高了,且兼蓄了《竹书纪年》的异闻,《周书•王会篇》的诡秘,《离骚》《天问》的远旨,南华、郑圃等地的寓言,写成此书。”
宋朱熹谓:“大氐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6]其意为:“大抵古今人注释楚辞《天问》,都根据《山海经》《淮南子》二书的记载。今以文意考索,疑《山海经》《淮南子》均为解释《天问》而创作,而此《天问》之语言,乃战国时期民间相传的俚俗之语。”
清代以降,又以多时期层累地成书说为主。纪昀(1724—1805)谓:“惟《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夏禹所记。其文稍异,然似皆因《列子》之说推而衍之。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嶲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欤?”[7] 其意为:“只有《隋书•经籍志》云,西汉萧何得秦火所余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为夏朝大禹所记。它的文字稍有不同,然都是根据《列子》的学说推衍而成。观书中记载夏朝第二任君主启、周朝文王及秦朝,汉代的长沙国、象郡、余暨县、下嶲诸地名,故《山海经》决不会产生于夏、商、周三代之前,当是周、秦之间的人撰述的,后来又有好异怪之徒加以续写。”
毕沅谓:“《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实禹书。禹与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类别草木鸟兽。”“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周秦所述也。”西汉“刘秀(即刘歆)又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于是其概述为:“《山海经》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于晋。”[8]
袁珂认为:“《山海经》不是出于一手,并且也不是作于一时,是可以肯定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至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年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于汉代初年。它们的作者是楚人,即楚国或楚地的人。”[9]
总之,现在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由于《山海经》内部所体现出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可以推论出,《山海经》是由民间口头文学流传而来,人们从荒蛮的远古时代起口耳相传,并在一代一代的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增益,书稿集成于战国之初,后历两汉、魏晋仍有修改增订。应当说,这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其中的具体内容,在有文献记载的商周以降部分较多得到整理与实证,而在无原始文献或文献稀缺的虞夏部分如“伯益撰《山海经》”“闽在海中”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二、“闽在海中”昙石山文化考古资料考释
王国维首创二重证据法。其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0] 那么,是否有地下的材料,可以论证《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谓的“闽在海中”?窃以为,答案是肯定的。
古今学者一般认为,无论是明言《山海经》为夏初伯益所撰或推测为洪荒时代的口头文学流传下来,其一部分内容可以追述至夏初。夏王朝纪年约为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那么夏初距今为四千余年,为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具体说就是昙石山文化时期。
据近五十年来的福建考古发掘,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已初步廓清,“大体可以区分为两大体系,一是面向海洋的东部体系,一是面向内陆的西部体系,这两大体系的分野,同由闽中大山带所造成的地区分隔,基本上是吻合的 [11]。”
(一)面向海洋的东部体系
其面向海洋的东部体系,文化类型基本为贝丘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1.早期
早期的代表为亮岛文化,其主要考古资料有《妈祖亮岛岛尾遗址群第三次发掘报告》[12]《马祖列岛自然环境与文化历史研究》[13]。
对此, 杨琮认为:“ 到了距今 8300— 7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段,福州地区出现了原始社会的‘亮岛文化’。这是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马祖列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亮岛上发现的。前后两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了四处史前时代的‘贝丘’遗址。他们在遗址中不仅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贝壳堆积,其中还有许多动物和鸟类的骨骼以及人工制作的骨器等遗物;同时还出土了一批早期的印、划纹和涂红的夹砂陶器残片,也出土了一批石器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两座年代不同并保存有人类骨骼的墓葬。亮岛遗址的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填补了福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历史的空白,建构起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历史文化的坐标。亮岛,这座位于马祖列岛中的并不起眼的小岛,遂即成为中国福州一个远古海洋文化的名称。”[14]
2.中期
中期的主要代表有平潭壳头遗址,距今 6500 年至 5500 年 [15],考古资料有《福建平潭壳丘头发掘简报》[16]《2004 年平潭壳丘头遗址发掘报告》[17]《壳丘头遗址人骨观察》[18] ;平潭西营遗址,距今 6800 至 6500 年 [19],考古资料有《1992 年福建平潭岛考古调查新收获》[20];金门岛富国墩遗址,距今 6300 年至 5500 年,考古资料有《金门富国墩贝冢遗址》[21];等等。
对此,林公务认为:“壳丘头文化遗址地处平潭岛湾海岸山麓坡地上,面积不到三千平方米,是个小遗址,文化堆积较薄,且主要堆积物为贝壳,其中夹不少兽骨及部分文化遗物,灰层少见。文化内涵比较简单,同类遗址如平潭南厝场、金门富国墩,还有粤东北的潮安陈桥等处 [22],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性质。这些遗址均地处滨海沿岸或海岛上,背靠大山,面向海洋。山上的采集狩猎,海岸边的捕捞采贝,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有农业存在。”“上述诸要素所构成的壳丘头遗存的文化内涵及其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与该遗址属于同一性质的同类遗存,如富国墩、陈桥等有相似的文化特征外,目前尚未发现于其他文化之中,是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文化,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壳丘头文化’。尽管迄今此类遗址所发现的点还不太多,但就这些零星的点来说,已经给我们大致指出了一个此一文化分布的空间范围,即该文化主要分布福建中、南部及南达广东东北部的沿海地区。”[23] 这里有两点可注意者:一为原发性,即壳丘头文化内涵及特征除其外延至广东陈桥遗址外,尚未发现于其他文化中,是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文化;二为空间分布,主要分布在福建中、南部及南达广东东北部的沿海地区。
3.晚期
晚期的代表最典型的为昙石山文化,距今 5500 至 4000 年 [24],考古资料有十一次考古发掘报告的汇集本《昙石山遗址——福建省昙石山遗址 1954 年—2004 年发掘报告》[25]《关于福建史前文化遗存的探讨》[26]《闽侯昙石山遗址发掘新收获》[27]《昙石山遗址第十次发掘出土的哺乳动物》[28]《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兽骨》[29]。
昙石山文化其他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福清东张遗址下层,其年代约与昙石山文化相近,考古资料有《福建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30]《福清县东张镇豸寺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11—39 探方发掘报告》[31];闽侯白沙溪头遗址下层,距今 5500 至 4000 年,考古资料有《福建闽侯白沙溪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32]《闽侯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33]。
福州地区为昙石山文化的密集区,即中心地带,其遗址尚有闽侯庄边山遗址下层,马祖列岛炽坪陇遗址,闽侯大坪顶遗址中层,连江县透堡镇馆读村黄岐遗址 3、4 层,闽侯白头山遗址,闽清南文墩遗址,福州市区淮安遗址,福州市区浮村遗址,福州市区横屿遗址、闽侯县洽浦山遗址,闽侯桥头遗址,闽侯赤塘山遗址,闽侯凤山遗址,闽侯牛头山遗址,闽侯寨垱遗址,闽侯鸡公山遗址,闽侯象山遗址,闽侯西塘山遗址,闽侯上街岐头遗址,连江贵岭遗址,连江狮山遗址,连江云居山遗址,连江岗头山遗址,平潭苏澳崎遗址,平潭马鞍山遗址,平潭湖南边遗址,等等。[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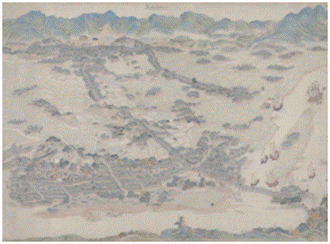
约绘于17 世纪下半叶的《福州全图》
关于昙石山文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形态,曾凡认为:“现根据这种文化的综合分析,大致已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了。”“有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和渔业,而这些生产部门在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各遗址中都有发现为数较多的石锛、石斧、石镰、石刀、蚌刀、贝耜、陶网坠等。这些都是用来从事农业或渔业的一种生产工具,而且有大量而很厚的贝壳堆积。”“有了比较发达的狩猎业和畜牧业,而这些生产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在遗址中,不但发现有用于狩猎而式样众多的石镞和骨镞,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种兽骨。这些动物骨骼,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计有狗、猪、豪猪、棕熊、虎、印度象、梅花鹿、水鹿、犀、牛、叶猴、鳖等。”“有了纺织业、缝纫业和制陶业的技术。根据各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陶片、纺轮和骨针等,可以得到证实。特别是制陶技术已经在慢轮修整基础上,创作了转动比较快速的陶轮,采用这种陶轮制作的陶器,厚薄较为均匀,器形也较为规整和精美。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从其出土的数量之多,可知这种手工业在当时也是很普遍而发达的。”[35]
关于昙石山文化时期的人口数量,王银平根据目前发现的昙石山文化时期遗址、墓葬的数量,以及遗址的占地面积(包括当时福建省内其他地区遗址)等资料进行的分析推算,得出了“福建昙石山文化时期人口规模在 13822 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 3 人 / 平方千米”[36] 的结论对此,杨琮认为:“我们认为如果仅从以福州地区为主的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先民的人口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还比较接近。但是他所指出的是福建全域当时的人口数,显然不够准确了,而且可能相差甚远。”[37] 我以为这个数字估计偏低,因为它是基于已发现的遗址、墓葬数量来分析推算的,当尚有很大数量的遗址、墓葬未被发现,姑且加上一倍,为二万五千人。当时,在福建新石器代时代晚期,此一东部沿海型的昙石山文化是最大、最繁荣的文化,而西部的内陆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就相对薄弱,以当时福建省西北部、西南部的人口统括之当亦不超过昙石山文化之人口数,姑且亦算为二万五千人,则当时全省人口数当在五万之内。
在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上,由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为西部、北部大山阻挡,由于福建新石器时代进程发展相对缓慢,在昙石山文化时代其尚保有某种独立性。对此,杨琮谓: “昙石山文化明显是由亮岛文化至壳丘头(昙石山下层文化)一脉相承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并不排除它会与闽北牛鼻山文化等临近地区的原始文化互相交流和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是非常有限的。”[38]
(二)面向内陆的西部体系
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东部地区有本质的区别,对此由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考古六十年•福建省》有精要的概括,其云:[39]
闽西北地区多为山间河谷的山岗遗址,相继发掘了明溪南山、南平宝峰山、浦城牛鼻山、浦城黑岩头、武夷山葫芦山、武夷山梅溪岗、邵武斗米山、浦城连墩遗址、连城草营山等遗址。距今 5000—4000 年前牛鼻山文化与距今 4000—3500 前的马岭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
牛鼻山文化在闽西、闽北分布较广,典型遗存有南山、牛鼻山、梅溪岗下层、浦城连墩等遗址。牛鼻山遗址位于浦城县管厝乡党溪村牛鼻山南坡,1989、1990 年先后两次发掘面积 900 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19 座,灰坑 8 个,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遗物 300 多件。牛鼻山文化有自己的鑇特的风格,同闽江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昙石山文化有明显的差异,与毗邻的江西、浙江等地的同时期新石器文化有相似之处。
在邵武米山遗址发现类似于干栏式房屋遗迹一处,以及一批同时期的竖穴浅坑式墓葬。出土随葬器物有陶器、石器、玉器等。玉器随葬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发现,几乎每墓均有,最多的一墓达 6 件,这种情况是福建以往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所少见的。
马岭类型(或肩头弄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过渡时期,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至商代早期,距今 4000 年—3500年,在光泽马岭、邵武斗米山上层、武夷山的葫芦山、浦城的猫耳弄山等遗址都有发现。其以黑衣陶为主要特色,出现了甗形器、敞口尊、曲腹盆、圜底钵、鱼篓罐、虎子等新的器物组合。在葫芦山的遗址中发现了有平面呈葫芦形、个别呈圆形或长条形的陶窑,在猫儿弄山窑群甚至出现了长达七八米的龙窑,窑中出土了黑衣陶、赭衣陶、红衣陶和彩陶器。
这里首先要正名的是,夏王朝初年所指称的“闽”为闽族,他们仅仅生活在今天福建的东南部濒海地区及其近海的岛屿上。而今天福建面向内陆的西部地区被称为“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即“闽”西北方向的山区。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文化是牛鼻山文化及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马岭文化。牛鼻文化,一则有自己的风格,二则与昙石山文化有明显的差异,三则与毗邻的江西、浙江同时期的文化有相似之处。对后者,有学者谓:“牛鼻山类型与昙石山文化有较大的差异,而与江西樊城堆类型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40]又有学者谓:“在牛鼻山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以赣鄱地区为中介的、来自长江中下游崧泽、北阴阳营、黄鳝嘴、薛家岗和屈家领文化的影响。”[41] 显然,这一地区在夏初并不包括在闽的范围内。
马岭类型文化则与牛鼻山文化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综上,经二重证据考释,可知数点:
第一,《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载的“闽在海中”是信史,其泛指福建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先民生活在今天近海亮岛等地,中期生活在今天平潭岛、金门岛等地的先民;特指晚期生活在东南沿海等地的先民,故“闽”特指为新石器时代昙石山文化下的先民。其后转化为地名。
第二,“其西北有山”系指西北内陆地区有高山,这一内陆山区在“闽”之西北方向,故其当时本身不是闽。
第三,“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早期、中期,居于海岛,山在海中自不待言,关于后期,据地理学家考察、研究,“冰后期气候回暖是渐变的,由于气温回升,陆地冰雪消融,海面因此上升,产生了冰后期最大一次海进。福建全新世海进一般认为是距今 5000—6000年前。海进时,海面高出现今海面 2—5 米,福州盆地和漳州盆地都成为浅海湾,海湾中散布着许多岛屿,而今以‘屿’命名的地方,如前屿、后屿、南屿、台屿、横屿、厚屿、盘屿等,当时均为岛屿。”[42] 就今天的福州盆地而言,其时闽江的入海口退至北沙、甘蔗一带,海水直达北峰山麓,福州盆地成了一个大海湾,露出海面的只有屏山、乌山、于山、高盖山、大顶山、妙峰山、旗山等,其他的昙石山文化滨海地区也大致相同,故“闽中山在海中”。
第四,夏王朝伊始,中原地区进入历史时代、即文明时代,其时福建尚处于史前时代,其大约在战国时期才进入历史时代。“闽”是中原夏王朝文明对福建东南沿海昙石山文化先民的称谓。
第五,在福建历史上新石器时代晚期,滨海亮岛文化、壳兵头文化、昙石山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海洋文化,其一脉相承,相对独立,具有独特的个性。而西部山区的内陆文化如牛鼻山文化、马岭文化则比较薄弱,而且不断为邻近省区的文化所同化。相对而言,最早被称为“闽”的昙石山文化先民,是福建先民最重要的代表,后来其一部分播迁海外成为南岛语族的滥觞,一部分为战国之际南下的越族所融合成为闽越族。
第六,历代研究者始终有人坚持《三海经》发端于唐虞之际、夏初的伯益,颜师古注云“即今泉州是其地也”,吴任臣谓“知洪荒之世,其山尽在海中”,现证明均为灼见。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2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注:
[1]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2,第 237 页、238 页。
[2](夏)伯益撰、(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传》卷 1《南山经》,经训堂丛书汇印本。又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山海经叙录》:“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出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清嘉庆十四年阮氏琅环仙馆刻本。
[3]黄晖《论衡校释》卷第十三《别通篇》,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0 年 2 月,第 597 页。
[4]崔治译注《吴越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 5 月,第 153 页。
[5](明)王应麟《明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本社出版,2009 年 4 月,第 314 页。
[6] 朱傑人等主编《朱子全书》19 册《楚辞辩证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本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 9 月,第 202 页。
[7](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 月,第 3623页。又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42《子部 5五十二•小说家类三•同海经十八卷内府藏本》。
[8](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嘉庆四年(1794)经训堂刊本。
[9]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 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71 页。
[10]王国维《古史新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 4 月,第 2 页。
[11]林公务《福建境内史前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区系类型》,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3 月,第 71 页。
[12]陈仲玉《妈祖亮岛岛尾遗址群第三次发掘报告》,[ 台湾 ] 连江县政府出版。
[13]陈仲玉、刘绍臣《马祖列岛自然环境与文化历史研究》,[ 台湾] 连江县政府出版。2016 年。
[14]汪征鲁、薛菁主编,杨琮撰《福州通史•先秦卷》,第 14 页。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5]同 [14],第 124 页。
[16]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潭壳丘头发掘简报》,《考古》1991 年第 7 期。
[17]福建博物院《2004 年平潭壳丘头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9 年第 1 期。
[18]陈盛、范雪春《壳丘头遗址人骨观察》,《福建文博》2021 年第 3 期。
[19]同 [14],第 127 页。
[20]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厦门大学考古专业《1992 年福建平潭岛考古调查新收获》,《考古》1995 年第 7 期。
[21]以上均见林朝棨《金门富国墩遗址》,台湾:《考古人类学刊》,33/34 期,第 31—36 页,1973 年。
[22]莫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 年 11 期。
[23]林公务《福建境内史前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区系类型》,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3 月,第 71、72 页。
[24]林公务《福建境内史前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区系类型》,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3 月,第 74 页。
[25]福建博物院、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编《昙石山遗址——福建省昙石山遗址 1954——2004 年发掘报告》,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书局,2015 年 12 月。杨琮注:报告中第 9、11页,书中所说的第九次发掘,实际上是第十次发掘;写到了 2010 年昙石山最后一次发掘,却把它归为第十次发掘,实际上是第十一次发掘。在综合报告书标题上则应该标明是 1954—2010 年发掘报告。
[26]曾凡《关于福建史前文化遗存的探讨》,《考古学报》1980 年第 3 期。
[27]陈存洗、陈龙《闽侯昙石山遗址发掘新收获》,《福建文博》1983 年第 1 期。
[28]林凤英《昙石山遗址第十次发掘出土的哺乳动物》,《福建文博》2012 年第 2 期。
[29]祁国琴《福建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兽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代人类》第 15 卷第 4 期,1977 年 10 月。
[30]均见福建省文管会《福建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 年第 2 期。
[31]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福清县东张镇白豸寺新石器时代遗址第11—39 探方发掘报告》,《厦门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59 年第 1 期。
[32]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白沙溪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4 期。
[33]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 年第 4 期。
[34]同 [14],第 300—342 页。
[35]曾凡《从考古发现谈福建史前社会的发展问题》,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州教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 54 页。
[36]王银平:《福建昙石山文化时期人口规模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福建文博》。
[37]同 [14],第 380 页。
[38]同 [14],第 245 页。
[39]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考古六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9 月,第 287、288 页。
[40]郑辉《福建浦城牛鼻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6 年第 2 期。
[41]付琳《武夷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南方文物》2023 年第 2 期。
[42]福建省地方志委员会编《福建省•地理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12,第 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