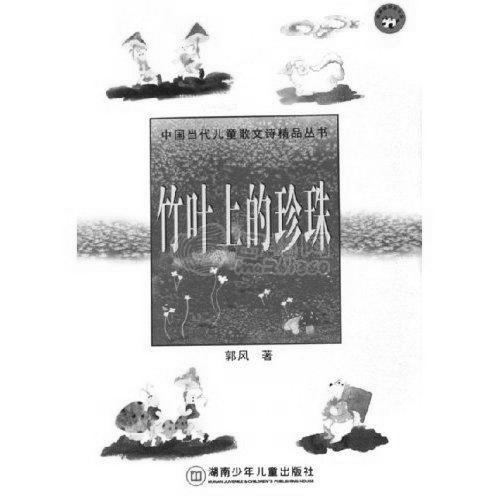广种福田——悼念郭风
季仲
榕城这个阴冷的冬天,享年93岁的郭风老人驾鹤西去了。虽然几达生命的极致,虽然终结才是对于病魔纠缠的一种解脱,然而,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那慈祥的笑容,听不到那亲切的声音,心头难免涌起沉重的哀伤。
郭老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程,说他主要做过两件事:写作与编辑。如果问其侧重点,他会补充说,第一是编辑,第二才是写作。然而,因为郭老的散文创作闻名海内外,在某种程度上把他在编辑方面的卓越贡献掩盖了。我作为他的编辑同仁,我在为老人送行的时刻,仿佛回到往昔岁月,想起在他手下从事文学编辑的许多旧事。
郭老的编辑生涯,最早当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1941年受聘为永安华南通讯社编辑,1944年任福州改进出版社《现代儿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文联甫一成立,他即协助鲁岩创办《福建文艺》,担任副主编。1960年夏,我进《热风》(由《福建文艺》改名)当编辑时,郭老仍任副主编。从此,我有缘在郭老手下工作20余年。
半个世纪前的郭风刚过不惑之年,在《热风》编辑部已算首屈一指的长者。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体态略胖,目光睿智,恂恂然有儒者之风,与小编辑们相处没有一点架子。那时省文联设在鼓屏路14号一幢小院里。院内有一株芒果树,一株白玉兰,一到盛夏季节,都会将散发着清香的绿叶伸展到我们窗前。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正如老作家林芹澜所说,文艺界有个短暂的“小阳春”,政治环境稍稍宽松了些,编辑部的人际关系也挺融洽。就像那株芒果树与白玉兰带给我们一片清凉的绿荫,那些日子给我们留下许多温馨的回忆。
在病床上的郭风
郭老与主编张鸿共用一间办公室。室内摆设因陋就简,书案与沙发都破旧得有些寒碜。郭老那时还兼任文联秘书长,须处理一些行政冗务,刊物主要由另一位副主编苗风浦主管。但一得空闲,他总爱到编辑部各个房间串门,捧一杯茶,燃一支烟(他年过半百于文革“牛棚”中才戒了烟),也不坐我们让过的椅子,就那么站着或来回走动着与我们聊天。除了时政要闻、坊间趣事,大都是谈他年轻时候读过什么书,喜爱什么刊物。他说到自己深受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的影响,开始热爱文学;谈到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处女作散文《地瓜》,从此走上创作之路;他终生感激不尽的是黎烈文主编的《现代文艺》以及当时的执行编辑王西彦,在短短三年之内,连续刊发他几十篇散文与散文诗。郭老说,一个编辑刊发一篇好稿,往往会发现一个作家;相反,如果错过一篇好稿,也许就此埋没一位天才。郭老还常常强调,对于出类拔萃的作者,要让他们吃小灶,连续集中刊发他的作品,这样就能造成影响,推出一个作家。他叮嘱我们要学会查阅古籍。他说古典文学浩如烟海,能过目不忘熟记于心的毕竟是少数,能记得哪个典故哪句名言哪篇诗文的出处,知道查阅,编辑与写作都很方便了。他说编辑用错一个词一个字,贻笑大方事小,误人子弟事大,所以要勤翻词典。他甚至不为己讳,说自己乡音难改,常常读错字读错音,以此教育青年。郭老一向谦逊木讷,不擅长篇大论,我几乎没有见过他所写的专谈编辑经验的文章。但他这些散文随笔式的闲谈,就是最好的编辑启蒙课,让我一辈子受益无穷。
“文革”结束,《福建文艺》复刊,文联的书生们陆续从下放地调回重操旧业。那两三年间,小说散文组十余位编辑都挤在一间大办公室。郭老坐在西头临窗书桌,我坐在东头临窗书桌。我们与郭老天天见面,由他言传身教,受益就更多了。
当时,数千万已经返城或尚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对于文学怀有空前热情,因此每天来稿堆积如山。然而郭老桌上几乎不留积稿。一是他从不读长稿,拿到小说或长散文都推荐给其他编辑。二是他读稿极快,一目十行。但他决不会错过好稿。对于稍有基础的稿子,总是来稿必复。不过信写得极短,字却很大,总是三言两语。像他给无数业余作者的作品集所撰的序言,循循善诱,激励后生,暖人胸怀。郭老没有任何体育爱好,也从不参加我们工间操时的球赛娱乐。他看稿看累了,就在编辑部的走廊散步,或站着写退稿信。他说站着写信也是一种休息和运动。若干年后,我遇到不少作者朋友,都说他们至今珍藏着郭老的信件,不时展阅,如沐春风。
郭老既重视发现新作者,又提倡多发名家佳作。他说,商品都讲名牌,刊物上更要能常常见到名家新作。由郭老倡议,《福建文学》从1980年起,每年推出一期散文专号或专辑。(这一风格传承至今,令人欣慰!)在这些专号上,我们屡屡见到巴金、冰心、郑敏、汪增琪等等大家的散文佳作,让《福建文学》大放异彩。那都是郭老约来的稿子。与此同时,专号上又能见到许多刚刚冒尖的新作者。那时各省以至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总是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拼盘,而小说是重头,留给“散文”的篇幅十分有限。郭老就把新作者的好散文积攒下来,让他们在散文专号上崭露头角。有着菩萨心肠的郭老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就是办散文专号时说的。
新时期文学的头几年,郭老除担任《福建文艺》编辑,还任过省作协主席、省文联党组成员、省文联秘书长,数职在肩,事务繁多,而他仍单枪匹马创办《榕树文学丛刊》。窃以为,此刊的存在与贡献,是福建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迹。说句戏言,它当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四无”刊物:一无刊号、二无专职编辑、三无专项经费、四无办公场所,甚至,连实际上的主编郭风也从不在刊物上署名。没有刊号,郭老就争取当时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杨云同志的支持,请他每期批给一个书号,以书代刊,大32开本,全国发行。没有专职编辑,郭老就抓弟子们的差,如章武、和平、文山、谷忠、唐敏、志坚等,均曾聘为业余编辑,是郭老的得力助手。1979年到1983年这短短四年,《榕树文学丛刊》出版散文专号、诗歌专号、散文诗专号、民间文学专号共13辑。每辑以20万字计,共260万字,从约稿、编稿、审稿到付梓校对出版,那是一项多么浩大的文字工程!我至今记得,当时在编务组放置信件的案头上,郭老每天发出的信件都是一大摞,收到的稿件也是一大摞。那时郭老已是年过花甲的老者,身体并不壮实,办刊又无分文经济效益,但他却孜孜不倦,为文学为后人作出纯粹而高尚的自我献身!
与此同时,郭老与刘北汜联合策划主编出版《曙前散文诗丛书》,与柯蓝联合策划主编《黎明散文诗丛书》,都是无可替代的文学选本,填补了某个历史阶段散文诗的空白。
郭老倡导的《福建文学》散文专号与主编的各种散文书刊,其重大贡献决非限于福建一省的文学繁荣。我以为,就全国来说,他推动了当代散文的发展与散文诗的勃兴;就福建来说,他发现和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为建设起一支蔚为可观的散文家队伍奠定了基础。这都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
当然,郭老更大的贡献还是散文创作。特别是他步入老年,迎来自己第二个创作高峰。我在一篇读书随笔《秋天的景象》中,盛赞郭老拥有一个色彩绚丽硕果累累的文学秋天,生命秋天。这篇短文记述郭老在年过花甲之后,青春焕发,迎来自己第二个创作高峰。他的“叶笛”又吹响了,在全国各大报刊上连续发表《松坊溪的冬天》《水磨》《溪景》《月亮》《彩色的溪卵石和鱼》《山中叶笛》《雪天漫笔》《松坊村初雪》等等散文与散文诗,有如喷泉在阳光下喷发万点水花,呈现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瞩目。回望当代文坛,像郭老这样在步入老年之后,仍然新作迭出同时又编辑那么多书刊的散文家,几乎独一无二。
日后,我时时想起,郭风老人是以怎样神奇的精力处理那么多文稿?同时又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当我在记忆深处拾起一件小事,答案便了然于心。我与郭老在同一间编辑室工作的年代,曾看到郭老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他亲笔手书的一则座右铭:“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后来我东施效颦,也把此诗抄录在寒舍书案的玻璃板下以资自勉)于是我便想到,淡泊清苦有如陶潜的郭风,无论读书、编辑或写作,都是惜阴如金夜以继昝无比勤奋的。约有十个春秋,我与郭老同时寄寓于福州黄巷18号,那是古代文化名人黄璞、梁章巨曾经住过的一幢深宅大院。1975年,《福建文学》在此院后进的废墟上建起五层宿舍楼。郭老住在东头501单元。郭老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我们常常看到,每天清晨天才微微放亮,五层楼上的郭宅窗前,一缕昏黄的灯光就与启明星一道,早早地透出朦胧的暖意,为这片飘逸着千年书香的古坊名巷增添几分曙色。可见这位著名的散文家、编辑家,为文学事业是何等的呕心沥血!

郭风著作
郭老除了编书编刊,提携后进的宽大胸怀,章武、文山、谷忠诸君的文章中已多次写到,而对敝人的深恩厚泽我亦没齿难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一些不成气候的小说散文习作,不少是经郭老举荐而在全国性刊物刊发或选载的。 199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沿江吉普赛人》出版,极少阅读长篇的郭老竟浏览一遍,并写了评论《长篇小说的人物、抒情及其他——读季仲〈沿江吉普赛人〉》,溢美之词,奖掖之情,令我汗颜。郭老之润物细雨,甚至惠及我的子女。1998年春节,我率小女到郭府拜年,郭老得知小女正在准备报考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非常高兴,立即将一套珍藏多年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赠予小女,并谆谆教诲,成为有力的鞭策。郭老对其得意门生袁和平、唐敏的关爱备至,在文联更是传为佳话。对于文学偏才,郭老一向有自己执著的主见。他说,十全十美的全才是不多的,天赋都各有所专。他以自己为例,说他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却在文学上走出自己的路。郭老推己及人,以此律人,对他的部属就非常宽容。和平与唐敏,乃璞玉浑金,经郭老呵护雕琢,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勤奋努力,终成大器,写出各自漂亮的小说和优美的散文。
除了文学,郭老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他一辈子都在伏案劳作,一辈子都在书斋度过,为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了晚年,即使世俗社会,追名逐利,物欲横流,郭老也像一代高僧坚守一方净土,坚守着文学的纯洁与崇高。对于文学编辑的意义,他的诠释也带有佛学的深刻与玄妙。他多次对我说过,一个文学刊社的编辑就是“广种福田”。佛家主张行、住、坐、卧,处处都要广结善缘,广种福田。佛家以慈悲为怀,把自己善良的愿望像种子一样播种在田土里,求众生得福,祈众生成佛。这个比喻是多么贴切而精辟!郭老对待文学,对待写作与编辑,一如敬仰一种神圣的宗教,始终虔诚谨恳、兢兢业业,为此付出了一生的辛劳。
广种福田自有福。郭老,您一路走好!您的一生,是广种福田的一生,也是种福得福的一生。我们——您的弟子、同道和读者,将会永远记住您的名字——郭风——那位用叶笛“吹出了对于乡土的深沉的眷恋,吹出了对于故乡景色的激越的赞美”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