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魏世英
房向东

魏世英
转眼,魏老先生魏世英去世已经6年了。这期间,时不时想写一点文字,以表达对他的谢意和敬意。然而,忙这忙那,写了几百字,没有写下去。
前些天,整理书柜,发现我竟然还保存着一整套《当代文艺探索》,翻了翻,隐约可见魏世英的魂魄游走在字里行间。当年,中国文坛“北有《当代文艺思潮》,南有《当代文艺探索》”。“思潮”兴,“探索”盛,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当代文艺探索》是不死的,魏世英就活在这本刊物当中。
80年代中期,我初出茅庐,魏世英已经是福建文坛的大人物。他先是当《福建文学》的副主编,后创办了《当代文艺探索》,蜚声中国文坛,浩浩荡荡,造就了一批“闽派评论家”。

魏世英任主编的《当代文艺探索》
当年,我认识他,他不知道我。通常,他是在台上发言,我只能远远地聆听和仰望。
除了办刊、搞文学评论以外,魏世英还偶尔写杂文。印象中,他的杂文是作家的杂文,不少是文艺随笔,形象可感,不像纯粹的杂文家,思辨大于形象。几次听他说话,大约都是在有关杂文的会上。他干瘦如柴,蹙眉冷眼,神色凝重,满脸沧桑,长得确实很像杂文。
第一次与魏世英搭上话,就关乎我的人生大事。
怀念魏世英80年代末,我所在的一家综合性月刊被“停刊整顿”,复刊遥遥无期。我进入“退休”状态,基本上无事可干,好在犬子如期而至,我在家相妻教子——天天为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洗澡,做操。
某日,在台湾饭店开一场海峡两岸作家的座谈会。会开一半,台湾饭店的老板(也是作家)冯秉瑞对我说:“魏世英叫你出去一下,他有事找你。”
我走出会场,魏世英和我握手,笑道:“知道你,今天才对上号。”我说,我老早知道魏老师,但是没有机会搭上话哩。
魏世英直奔主题:“你现在没事干吧?”
我说是的。
他说:“要不要调到省文联一起办刊?”
诸位看官,这可不是一件人生的大事吗?
他告诉我,他主办的《当代文艺探索》停办了,要改名为《文化春秋》,由理论刊物变成纪实刊物。我会写报告文学,也会写杂文、散文,刊物需要我这样的人。他还对我说了改刊的原因,强调海南也有一本纪实类的刊物,办得热火朝天,福建省文联也想有所作为。
看来,魏世英平时有关注我。被前辈关注,我心存感激,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困厄之中,并不相识的魏世英向我伸出了拯救之手,温暖之手,赏识之手,这真乃雪中送炭啊!
我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自然立马应允,说能去省文联工作,能到他麾下效力,是我的荣幸。
当时的省文联领导对魏世英非常尊重,马上同意,立即外调。
天上掉馅饼,工作调动竟是这么简单,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可惜,与文联无缘。真要走了,我所在单位的主管领导不同意放人。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我非走不可!”领导见我去意已决,说:“要走也可以,要等新刊办了3期后才可以走。”说我是新老交接的人物,要扶上马送一程之类。当然,这是客气话。话说到这一步了,我还能怎样?可是,现在不让走,过了这一村,就没了这一店,将来谁扶我上马?谁送我一程啊?
1991年,新刊面世,我就开路。可《文化春秋》也短命,没办几期,又停刊了,改为《散文天地》。我错过了在魏世英麾下效力的机会,后来调到了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编童话与科幻图书,上穷碧落下黄泉,满脑子奇思妙想。
落魄之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交浅情深,不管成还是不成,此生定是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后来,我参与招聘大学生应有十多次,面对求职者,都会想起魏老先生,提醒自己应该怎样面对陌生人。
此后,魏老忙,我也忙,我又不爱参加文坛的各种活动。在文人圈中摸爬滚打几十年,还是不习惯与文人一起谈文学。文人聚在一起,是不是都有点假啊?有点酸啊?哪怕是出汗吧,文学女青年出的是香汗,而蠢笨如牛者,出的则是臭汗——这是读鲁迅《文学与出汗》的结果了。总之,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
魏世英退休以后,有几回文坛中人邀宴,我们有机会聚到一起。他说,他可能要出两本书,一本是他还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一本是他的散文集。他不想在福建出版,问我有没有可能帮助联系省外出书。我说,我会尽力的。后来,他没再提起这事。我也没多问。
在我心目中,魏世英既是作家、评论家,也是老编辑。他做过许多栽培人的工作。他主办的《当代文艺探索》,哪个“闽派评论家”没有在这本刊物亮相过?魏世英是这样一种文人,大音希声,他有大好文章,却没有大名,没有浪得虚名。况且,他又不擅于宣传自己,包装自己。读者可以到网上搜搜看,关于魏世英的文章,可以搜到的就是何镇邦的《读〈悲喜春秋〉忆故人》一篇。真是“寂寞身后名”啊!出版不景气,出版业内人士比文坛中人更清楚,要推销他的作品,还真有难度。
2012年底,我邂逅作家出版社的黎云秀,我们谈起魏世英的长篇小说《又悲又喜的故事》,说在她这耽搁已有时日,恐怕难以出版。我问原因,主要是写了福建“城工部”地下党,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需要专题报审。如果报审,就不是出版社所能把握的了,而且结论可能遥遥无期。
事有凑巧。不多久,魏世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见他。谈的果然是这部书。他实话实说,原希望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平台大一点,影响也会大一些。现在看来作家出版社不行了,拖了很久,一直下不了决心,希望我能帮助出版。他说:“这是我一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书中有自传的成分,有我的影子。这十几年,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写这部书,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总结了。廉颇老矣,唯有此事未了,实在是最后的牵挂啊!”话中带有颤音,可见用情太深。我当即表态说,我一定尽力,但“城工部”确实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我说,我请一个这方面的专家看一遍,再报告最终意见。
这是一本80多万字的大著,写的是抗日战争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工部”领导的地下斗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福州地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书中确实充满自叙传的色彩。当时,我还在社长任上,诸事猬集,无法通读全书。我抽看了若干章节,文字干净而且从容,内容都是作者生活经历的结晶。老实说,比场面上的一些所谓名家,不知要好多少倍!这毕竟出自《福建文学》副主编和《当代文艺探索》主编的手笔,而且是他的“独生子”。这不是墨写的书,而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血,字里行间,都是时代波澜,岁月沧桑,生命体验。
我下决心出这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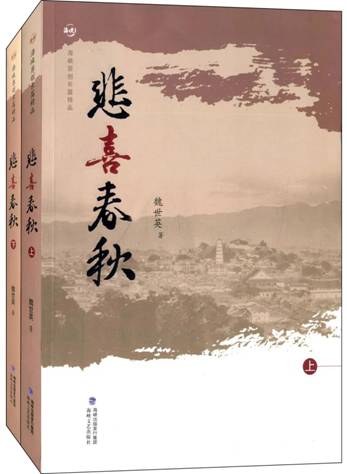
魏世英著的《悲喜春秋》
当年,我所在的出版社汲汲水养汲汲鱼,80多万字的大书,好歹得有不少的投入。说实话,这书是“小众化”的,要畅销,要不赔本,几无可能。
作为“当家人”,我想为魏老先生争取省里文艺基金的资助。我甚至私下已经与有关领导沟通,他们表示,像魏老这样的离休老干部、福建文坛的老将,当然应该给予支持。
我把这意思对魏世英说了,并说,不要他出面,我来与有关部门、有关同志协商如何?魏世英听了先是沉默,后是摇头,只说了一句题外话:“我退休以后,就没有再麻烦过文联……”
我听说,他退休之后甚至没有再进过老单位的门。我没有退休的经验,但魏老的行止是我需要效法的。
我明白了。他是个性很强的人,我只好不再运作。
后来,是他女儿出了最大的力,使得他的书得以出版。我猜测,魏老可能还不清楚这一点?
原书名叫《又悲又喜的故事》,我觉得稍长,建议改成《悲喜春秋》,魏世英欣然接受了。
魏世英的老朋友何镇邦得知魏世英去世,向我索要这部书,他还为魏世英和他的书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何镇邦说:“……作为这一历史事件背景的福州民俗风情以及关于秦家这一颇有巴金的《家》之艺术韵味的破落大家庭的描写,作者的笔墨似更自如,它所蕴含的闽都文化也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应看作福建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不会也不应被湮没。”何镇邦的意思,魏世英的笔墨要比《家》更自如。这是蛮高的评价。我甚至觉得,魏世英的叙述语言,要比《家》更好。
怎么让魏世英的这部书不被湮没呢?怎么让人重新发现这部书呢?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我请了一个既是福建党史专家又是“老福州”的老先生审读此书。他竟和魏世英交上了朋友。他边审稿边和魏老聊天,探讨相关问题,闲聊风土人情。他们聊得很深入,很开心。魏老对我说:“你为我找了一个谈话对手!”我的这位专家朋友,因为妻子瘫痪在床,审稿的时间拖得有点长,因而书的出版时间也拖了比较久。
负责审稿的专家朋友告诉我,魏世英的书是一生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反复修改、校对这部书。这一点,魏世英的老朋友、老同事季仲在回忆文章中也给予证实:“这期间,我造访魏府,每每见老魏弓着背、弯着腰、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电脑桌前,锲而不舍地敲着键盘。直至离其生命尽头前数月,这部八十余万字的《悲喜春秋》才出版面世。”
魏老先生的另一个朋友对我说,他生命的最后日子,全神贯注在《悲喜春秋》上。书出版了,他把书送出去了,觉得无所挂牵了,所以,他松弛下来,就走了。
季仲先生说,老魏是死于老病,属于寿终正寝。并说,他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很是可惜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安多纳德,当她把弟弟抚养成人后,就松弛下来,很快就多病并发,走了;我结婚后的一周,我多病的祖母就去世了;我退休前,一个老同志,也是捧到他一生中最后一本书后,就辞别了……
我想,如果《悲喜春秋》迟两年出,魏老也许还会多活两年?
(作者系福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